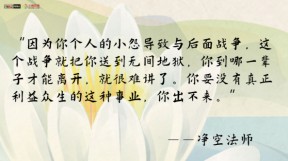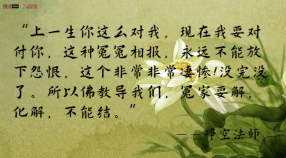我于一九五六年八月,当年我十九岁,高中毕业后就离家,从安徽省含山县到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,投靠虚云老和尚求出家。他老人家收我为徒,亲自为我剃度,取名宣德,号绍云。当年冬月去南华寺受具足戒,之后回云居山常住。几个月后,开始当老和尚的侍者。

老和尚到云居山后没几个月,来了五十多人,他们见了老和尚后都不肯离去。于是老和尚向政府申请重建云居山,获批准后随即动工。为了生活上能自给自足,便开始垦荒,种庄稼。我1956年去的时候,已经开发了近一百亩水田,六十多亩旱地;每年可收水稻六、七万斤,红薯和马铃薯七、八万斤。
当时,老和尚已高龄117岁,每天都亲自到建筑工地和开荒的山地去巡视和指导,还要接待来自各方的人士。晚上六点到禅堂讲开示,八点以后开始阅读各地来信,有时信一天多达百封,他老人家都一一过目。平常都到十二点左右才休息,翌晨两点又起床打坐,直至打四板(大约三点半),才起床洗脸。

当时,山上的生活很艰苦,开发的田地不多,收成的谷子也很少。因为红薯收成较多,每年七月开始到翌年三月,是吃红薯的季节。红薯的叶和枝是我们的小菜,有时连蕃薯和叶也没有,就只有把盐加进稀饭吃。
老和尚吃的稀饭和菜,都是我们从大寮打的,跟大众师傅吃的一样。他老人家这种节俭简朴的生活,现在想起还记忆犹新。
云居山地势很高,冬天气候很冷,气温常低到零下十七、八度。收藏在地窖的红薯和寒冷空气接触后,皮发黑煮熟后吃起来很苦。 有一次,我和齐贤师在老和尚那里吃稀饭,吃到那种又苦又涩的红薯皮,便拣出来放在桌边。老和尚看到时默不作声,待吃过稀饭后,他老人家一声不响地,把那些红薯皮捡起来吃掉。当时我们俩目睹此景,感到很惭愧、很难过。从此,再也不敢不吃红薯皮了。
事后我们问他:“您老人家都这么大年纪了,红薯皮好苦!您怎么吃得下去?”老和尚叹了一口气对我们说:“这是粮食啊!只可以吃,不可以糟蹋呀。”

老和尚的身体很好,早上除了吃两碗稀饭外,有时还会吃一点马铃薯。中午吃两大碗米饭。晚上吃一小碗面条或稀饭,过去他老人家一直是过午不食的,从云门事件发生后,他才开始吃药石。
他老人家很节俭也很惜福,他睡的草席破了,要我们帮他用布补好。不久同一个地方又破了,实在补无可补。我们想拿草席到常住去换一张新的。不料老人家知道后便骂:“好大的福气啊!要享受常住一张新席子!”经此一说我们都不敢作声了。
老和尚常开示我们:“修慧必须明理,修福莫如惜福。”意思是修慧参禅一定要明白道理,道理就是路头。想参禅用功,但路头摸不清楚,对参禅的道理未能领会,这样工夫便很难用上了。所以古人说:“修行无别修,贵在识路头;路头识得了,生死一齐休。”“造福莫如惜福”就是要珍惜自己生活上的一切福德因缘。他经常训诫我们说:“你们要惜福啊!你们现在能遇到佛法,到我这里来修行,可能是过去世积培了一点福报;如果不惜福,把福报享尽了,就变成一个没有福报的人。犹如你过去做生意赚了钱,存在银行里。如果现在不再勤奋工作赚钱,只顾享受,把银行的储蓄花光了,接著下去便要负债了。”

虽然,老和尚高龄一百一十多,但是他的气力却是无法测量的。曾跟随老和尚在云门寺同住的师父说,有一次他们在云门开荒,有一块大石头,好几个人都搬不动;老和尚来了叫他们走开,独自一人就把那块大石头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
1957年下半年有一天,我刚从外面回来,见到老和尚双手提着两大捆木柴向大寮方向走,便问:“老和尚,您老人家怎么到这里来搬木柴呢?”经我一问他就把木柴放下,回寮房去了。我便到大寮找负责砍柴的自性师,把刚才的情景告诉他,他很惊讶地说:“我砍了三大捆木柴,自己扛了一捆回大寮。还留下两大捆在茅蓬西面的路边,因为太重了,我连一捆也扛不起来,老和尚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,两大捆一起提起呢?”
后来我们把那捆柴一秤,一捆就有二百多斤。所以老和尚的力气是没法测量的。修行的人,环境愈是艰苦,道心愈是坚固,老和尚常说:“不经一番寒彻骨,焉得梅花扑鼻香。”

有时要运材料上山,遇有月亮的晚上,坐完养息香及四支香后,还要到山下三十里路去担。回来休息不到两个小时,又要上早殿了。早殿、早堂过后,早板香只坐半小时,又要打板出坡了。所以那时的生活很紧张、很忙碌,但是师父们的道心都非常坚定。
此外,晚上每两人一班,每班两个小时,轮流看守稻田,防止野猪来犯。那时山上的野猪、老虎很多,当稻谷快成熟时,野猪就成群结队来了。只要有一只野猪叫,其它几十只就闻声而至,大肆吞噬田里的稻谷子,如是一大片稻田转眼间就化为乌有。
虽然老和尚年纪那么大,还坚持加入我们晚上看守稻田的轮班工作。

老和尚在云居山行住坐卧时以身作则,并常上堂为大众师父讲开示,以实际行动来教育大众。
在云门事件中,他老人家的骨头被打断了好几处。在五六至五八年间,经常生病发烧,身上的旧患和骨折的地方疼痛不已时,他便躺在床上呻吟。可是一听说有人来见他,马上又坐起来,盘起腿来精神好得很,可以一谈三四个小时,一点也看不出病态。有时我们催促客人走,想让他休息。他反而不高兴说:“人家有事才来找我,等人家把事情说完了才能走。”可是客人一走,他又躺下来呻吟了。我们问他:“刚才人来你精神那么好;人才走,为何又这么痛苦呀?”他说:“这是业障呀!阎王老子也管不了我,我要起来就起来,要不起来就不起来。”实际上我们也感到很惊奇。
一九五七年正月,他老人家病得很厉害,永修县和省政府的干部都来探望,并派车想接他到南昌省立医院去看病。本来他不愿去,但是省政府的领导一再劝说和催促,才勉强答应。到了医院,接受检查,化验血型时,那些医务人员都感到十分惊奇。他们说:“听说这位老人家已经一百多岁了,但是他的血就像十三岁以下的孩童一样,我们从来没见过,这么大年纪的人有这样的血。”经过详细化验后,他们说老和尚的血是纯阳性的。而老和尚只在医院住了四天就回山了。他老人家的血型,直至现在仍是个谜。
中午休息时,他老人家有时也打昏沉,头向前俯甚至打鼾。有一次,我们听他在打鼾,便偷偷离开,拿著房里面的果品到外面边吃边玩。他醒后就这件事来骂我们。我们问:“刚才您老人家不是睡到打鼾了吗?你怎么会知道呢?”他说:“你心里打几个妄想我都知道,你拿东西到外面吃,我会不知道吗?”此后我们才相信,悟道了生死的人,已经破了五蕴。见他是睡着了,其心思却是明明了了,清清楚楚的。

当年,他老人家六十七岁,在终南山住茅蓬。戒尘法师,是一位讲大部经的法师,听说老和尚在高旻寺开了悟,便到终南山茅蓬找老和尚辩论禅宗的机锋语。老和尚听他把话说得很大,便对他说:“你的机锋辩论虽然很好,但这个不是你自己真正的工夫,在生死根本上作不了主,阎王老子不会放过你的。不要再多辩了,咱们俩坐坐看吧。”于是他们两人就在茅蓬里打坐。老和尚一坐,就是七日七夜,如如不动。而戒尘法师只坐了半天,双腿已经痛得不得了,心里妄想更是烦躁不安。
戒尘法师每天都绕著老和尚走几圈,好不容易才等到第七天,老和尚终于出定了。他问老和尚:“您在定中,是有觉知,还是没有觉知呢?若是有觉知,就不名为入定;如果没有觉知,那岂不是枯定,不就是所谓的死水不藏龙吗?”
老和尚说:“要知道禅宗这一法,原不以定为究竟,只求明心见性。若是真疑现前,其心自然清净。由于疑情不断,所以不是无知;也因没有妄想,所以不是有知。虽然没有妄想之知,但就是一支针掉在地上,也能听得清清楚楚;你每天绕著我走几圈,我都知道,只因疑情之力,不起分别而已。虽然不起分别,因为有疑情在,用功不断,所以不是枯定。虽然不是枯定,这亦只不过是用功路途中事,并非究竟。所以过去这七天,我只是觉得好像一弹指间就过去了,如果我一生分别心,便会出定。参禅办道的人,必须将此疑情,疑至极处,一旦因缘时至,打破疑团,摸著自家鼻孔,才是真正的道契无生啊!”此后戒尘法师就一直跟随老和尚,对他老人家非常信服和尊敬了。

1957年他们一起到云南去开办道场。云居山有些八十多岁的老师父都知道。他们说那位戒尘老法师很了不起,后来是预知时至,先向大众告假后,坐著往生的。
在云南时,老和尚经常一坐七、八天。有时人家有要事找他商量,就得用引磬为他开静,他才出定。因此,老和尚在云居山时,我们就问他:“是否有这些事情呢?”
他说:“是呀。”
我们又问:“老和尚您现在为甚么不入定呢?”
他说:“现在重建寺院,每天都有政府人员和其他人来找,我不出去不行,所以不能入定呀。”他还笑说:“如果我在这里一坐七、八天不起,一些不怀好意的人,当我死了,把我的色壳子搬去烧。这样这个寺院就盖不成了,所以现在我不敢入定。”
虽然,老和尚在云居山时,没坐禅入定七、八天,但他经常一坐就一整天不动。有时从夜里十二点左右开始坐,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起坐。所以他老人家的境界,不是一般凡夫所能知道的。

据说证了初果罗汉的人走路时,虽然你看见他双脚是踩在地上,但实际是离地有两分高的。那时也有人问我们:“听说了脱生死的人,走路时脚不触地,不沾泥巴。那么老和尚算是大菩萨了,你们经常随他走路,究竟他的脚踩不踩地?鞋子沾不沾泥土呢?”于是我们就很留心这些事情,并经过多次试验。
云居山的地都是泥巴,经常下雨,一般人走一趟回来,鞋子自然沾了好多泥巴;可是老和尚的鞋子从来不见有泥巴。奇怪的是,当我们走在他后面,注意他走路时,明明是见他的鞋子踩在泥巴上;但是回来后,我们再看他的鞋子,就是没沾半点泥巴。这其中的奥妙,我们至今还搞不清楚。

当时老和尚每天晚上(或隔一、两天),在禅堂讲开示。时间一到,叫香板一打响,不但我们种田的、在外面出坡的师父们都往回跑;就连天空的乌鸦也一群群地飞回来听开示。那时云居山的乌鸦特别多,屋顶和附近的树上,从茅蓬到禅堂的路上,乌鸦站得密密麻麻的,令我们寸步难行。有时要用杖枝动它一下,它跳一下我们才有路可走,否则,就要踩到它们身上。开示说完了,老和尚回茅蓬,乌鸦也回巢了。所以鸟雀也很有灵性啊。
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旬,天气酷热,一天老和尚忽然要到五老峰顶看地形。当时有晴空、净行、传印师和我等一共六人,我们就将一张靠背藤椅两根竹子绑起来,做成轿子让老和尚坐,我们分三班更替。出门时已近九点,天气很热,太阳很猛。我们心中暗想:“老和尚体质这么弱,天气又那么热,偏偏选上今天上五老峰顶,一定被太阳晒得很难受了。”奇怪的是,当我们抬起轿子的时候,天空飞来很多很多的乌鸦,奇妙。